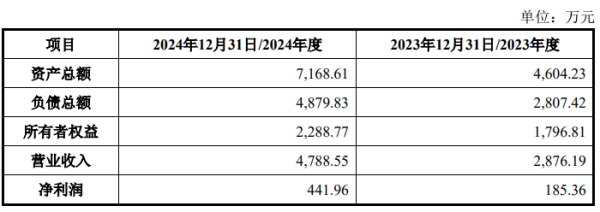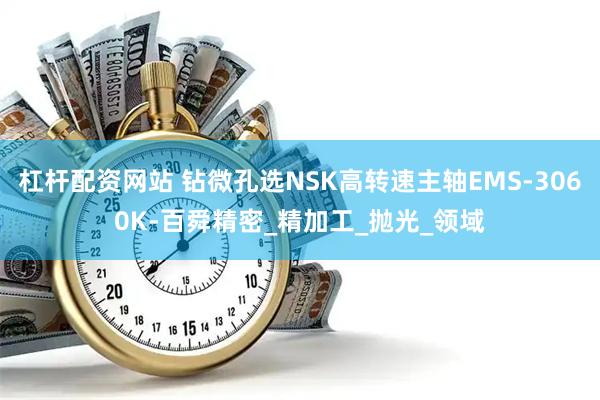【人物名片】王爽配资的论坛,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博士,现为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曾荣获北京青年五四奖章、首都绿化美化先进个人、全国绿化奖章、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并当选为北京市第十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王爽接受北青采访
颐和园植物病虫害测报站的办公室藏在北如意门附近的一处幽静小院里,办公室不算大,门窗仍保留着木结构,木格窗棂将天光筛成一缕缕的,轻轻落在室内。西侧的工作间里,养着王爽和同事们培育的昆虫,他们可以通过观察记录昆虫的生长周期和摄食特性,为“以虫治虫”等生物防治手段积累宝贵的一手资料。
颐和园有1607棵古树,最年长的已有600多岁。早在人类踏足之前,植物与昆虫就在这片土地上构建起了属于它们的秩序。王爽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维护好它们本来的秩序,守好植物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虫情测报员要每天转园子,树皮上的木屑、地上残留的黏液、叶子颜色的变化都是虫子留下的“密码”。虽然都是在园子里转悠,但虫情测报员的“转”跟寻常游客还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脚步更快,眼睛也很忙,会突然停下脚步盯着一棵树仔细观察,他们是颐和园里最关心树的那群人。
采访当天,我们经过颐和园长廊旁的一处刚搭好的施工区域,有几棵古树被围在里面,王爽立即停下来,趴在围栏上查看树况,随即联系相关人员询问情况,为什么施工?工期多久?对古树有没有影响?只要和树有关的事儿,她都格外放在心上。
博士的 "三重归零"
2008年,王爽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了颐和园工作。从小就怕虫子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和虫子打一辈子交道。其实,一开始她想学的是风景园林,后来误打误撞学了微生物专业,又在研究生期间转到了植物病理学。绕了一大圈,最后她还是回到了和自然打交道的路上。
王爽很满意这份工作,高高兴兴地就去上班了。“当时光顾着开心了,没想到还有很多困难等着自己。”她虽然是植物保护专业出身,但在学校主要学的是农作物相关知识,研究方向也是病害而非虫害,园林植物她不认识几样,对虫子更是一窍不通。来到生产一线,没有时间等她学透了再上手,只能边干边学。“虽然你是博士毕业,但是又能怎样呢?你还是要从头学起。” 她说。

工作中的王爽
防治虫害是工作的核心,做标本其实是熟悉虫子的好方法,但她根本不想碰虫子。高考前她曾被“洋辣子”蛰过,当时肿了半个多月,这段经历让她对虫子没什么好印象。选专业的时候她也刻意避开了昆虫学,结果工作后,还是和虫子遇上了。
怕虫子这关得过。
“遇到困难得想办法克服,不是说看到希望才坚持下去,而是说坚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她只能硬着头皮去做。“我到现在还记得做的第一个标本是斑衣蜡蝉,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当她亲手把标本做完后,强烈的成就感让她发现,虫子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整个过程甚至是想象不到的顺利。
从害怕恐惧到喜爱痴迷,王爽感叹这个转变太神奇了。她说,“其实这也是我们跟自然断裂的那一部分,通过和昆虫打交道我们又跟自然接上了。我们要了解自然,你不可避免地要去认识它、接触它。”

王爽在园林中踏查
记地名,记古建,对王爽来说是第三道坎。
他们的工作分白班和夜班。白班需要踏查、做虫情预报,而夜班则要配合白班执行应急防控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
颐和园小路交错,古建众多,她一上岗就要跟夜班同事交接,经常说半天也说不清树在哪儿、虫子是啥。“小地名一般是以古建为参照物,如果古建不熟悉,小地名记不住的话,那你肯定就描述错误,最后的防治作业就意味着失败。”
王爽憋着一股劲儿,为了尽快记住植物与昆虫特征,她转园子时会带着小本子随时记录,各班组打来的病虫害报告电话,她总抢着接,挂了电话就跑去现场查看,回来再复盘总结。在每天3万步的历练中,她走遍了有植物生长的每一个角落,花了一年多,颐和园里的树木种类和病害虫情况她已了然于心。
虫子的“二元论”
王爽的工作紧密围绕着园林植物和有害生物的生长规律展开。秋冬落叶后,树木进入休眠状态,落叶树的枝干清晰可见,常绿树也更容易观察,她和同事们便进行越冬基数调查和树木健康普查,既是为第二年病虫害防治做准备,也能在普查过程中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将防治工作前置。
春夏之交是一年里最吃紧的节点,随着气温回升,病虫害和天敌昆虫开始活跃。王爽和同事们需要应对双重挑战:既要监测干旱对树木的影响,又要防范早期病虫害的爆发。春天的活儿做扎实了,后面就能省不少力,之后再根据物候、天气预报以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判断是否需要人工干预。
颐和园西边的团城湖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也是南水北调工程的终点。为了南水北调,王爽的家乡南阳淅川先后有数十万人迁离故土。她从那里来,现在又在终点处守护着这汪水,守护着自己和家乡的纽带。
为了妥善处理绿地养护与水源涵养的矛盾,王爽带领团队探索零农药治理技术,以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而这也恰恰反映了近些年来病虫害防治理念的转变。

工作中的王爽
过去防治虫害,对益虫和害虫的比例要求严格,农药的毒性高、针对性差,药到之处无论益害都难幸免。现在农药用得少了,尽量让自然天敌发挥作用,通过引入瓢虫、肿腿蜂遏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蔓延,走的是生物防治的路子。
在王爽眼中,每种昆虫都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份子。所谓“有害”与“有益”,不过是人类基于自身需求做出的界定:当某种昆虫威胁到人类的生产生活,或危害到园林中的古树名木时,它便被视为“有害生物”,但对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它无所谓好坏。
她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赶尽杀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某一种生物,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只有它们的关系越复杂,彼此之间相互制约,这个生态环境才会更加稳定。”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让病虫害防治工作始终充满变数。气候变迁、人类活动、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都会让防治对象与发生态势呈现新的特征。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王爽和同事们在与病虫害的博弈中,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平衡:不求“大胜”,“打平手”才是更理想的状态。

工作中的王爽
一生只做一件事
从入了行,王爽就知道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事业。
有些昆虫的生长周期很长,完全变态的昆虫要历经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有的一年可以繁殖多代,有的数年才能完成一代。这意味着,病虫害防治工作不是只做一两年就能出成果的,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老班长魏宝洪是王爽的入门师父,这位自1985年起就在颐和园从事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前辈,手把手教她怎么找虫子,告诉她打药该打哪个部位才有效、在什么时机用药最省药。王爽说,“他一步一步带着你往前走,你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其实一生做这一件事已经足够了。”
王爽的身边,总有这样将一生热忱倾注于一事的前辈。她刚参加工作时,林业大学的李镇宇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坚持每周来颐和园带着大家一起踏查,帮大家分辨测报灯里的昆虫种类,教他们识别的诀窍。今年三月,李镇宇先生离世。王爽的朋友圈有三条置顶,都是和李老先生有关的内容,恩师的教诲,她从未忘记。

王爽跟随李镇宇老先生学习
她说,前辈们一辈子在岗位上坚守,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甚至在退休之后仍然觉得自己还没有把想干的事情做完。有这样的人在身边,她自然而然地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其实他们引领着我们,我们也在传承着他们的精神,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年轻的同志们。”
树的寿命比人的漫长,人只能短暂地陪伴它们一小段时间,然后还会有更年轻的人继续陪着它们。一代代人把一生奉献给这片园林,他们把自己的日子融进了树木的年轮里,最终也成为了树的一部分。
撰文 | 祝文琪
摄像 | 胡金童 翟天一
剪辑 | 胡金童
审核 | 姜泽菲配资的论坛
京海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